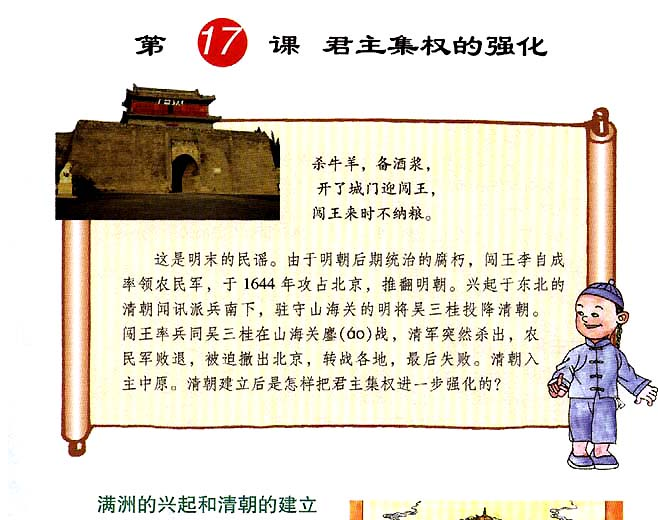近日,四川彭山江口镇1万余件文物出水,张献忠“江口沉银”的传说被证实。张献忠的历史形象,也将因这批文物而变得愈加清晰。
清初至民国,张献忠被视为“杀人魔王”
1、亲历者在笔记中,留下大量关于大西军屠杀政策的记录
最先对张献忠做出评价的,是那些亲历其统治者。曾在“大西政权”为官的欧阳直,著有《蜀乱》一书,历数张献忠的诸多暴行,如说他攻下重庆后,“尽屠其城。间有避匿得存者,查出复断其手”。曾追随明将杨展,同大西军作战的费密,在《荒书》中说,张献忠“尽屠川西、川北州县,以人手为功。凡贼验功之处,聚手如山;焚之,指节之骨,散弃满野”——大西军屠杀百姓后,留下一只手向张献忠请功,于是人手堆积如山;将人手焚烧后,散乱的指节漫山遍野。
2、清修《明史》,称张献忠“一日不杀人,辄悒悒不乐”
清人修撰《明史》,将张献忠列在“流贼传”中,并采信以上诸种笔记,称其“性狡谲,嗜杀,一日不杀人,辄悒悒不乐……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,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”。
3、民国时期,多数学者认为张献忠只有“混乱破坏”
进入民国,张献忠的历史形象,基本延续史家旧说。如鲁迅在1925年《灯下漫笔》中说,“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,不服役纳粮的要杀,服役纳粮的也要杀,敌他的要杀,降他的也要杀。”1935年,他又在《病后杂谈之余》中回忆,“我还是满洲治下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,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《蜀碧》,痛恨着这‘流贼’的凶残”。钱穆《国史大纲》引论中则说,“其他如汉末黄巾,乃至黄巢、张献忠、李自成,全是混乱破坏,只见倒退,无上进”,对张献忠没有一点好评。
在具体史料方面,民国学者有所辨析。清史名家萧一山在1927年出版的《清代通史》中,称张献忠为“流寇”,指其以屠戮为乐,但认为屠杀“六万万有奇”的说法“显系夸大”。在萧一山看来,所谓“七杀碑”,“即圣谕碑之讹传也”。1947年,四川学者任乃强作《张献忠屠蜀辨》,称其“粗识文字、知人善任、颇有志略、轻率易怒、好用谲术、个性强毅”。任乃强反对“屠蜀”之说,认为“当时蜀人绝灭之原因,盖死于饥馑者什七八,杀于献忠者什一二而已。”任是较早对张献忠持肯定立场者。①
1949~1980,犯过路线错误的“革命者”
1、众多学者致力于论证张献忠之“屠蜀”,所杀者全是地主官僚
1949年后,学术界对张献忠的评价发生重大改变。张被尊为反明抗清有功的“农民军领袖”。如1952年,谢国桢发表《张献忠与农民起义》,为张献忠辩解称:
“当时所谓张献忠喜欢杀人,‘醉柔而醒爆,无一日不杀人’,尤其是献忠帝蜀以后,杀人更多,光成都一带处就杀了百万人,四川人口去了十分之六,等等的话,这当然是统治阶级的污蔑宣传。我们从历史上观察,献忠两次入蜀,并不妄杀人,做了皇帝之后,正该安定人心的时候,何其反杀起人来?可见献忠所杀,完全是豪绅地主阶级;而且是两个集团做阶级斗争,地主劣绅迫着农民军走上这条道路……”。②
再如,1957年,孙次舟发表《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》,也说张献忠在成都杀的,都是“地主阶级的贵族和官僚”,原因是“因各县地主、官绅有武装反抗的图谋”;杀士子,是因为“发现士子中有不少奸细”,勾结清军。孙次舟还认为,造成四川人口灭绝,地方残破的主要原因,是清军、明军、吴三桂军的相互攻杀,只是“清初的官僚,都知道掩盖自身罪恶的办法,把破坏四川的责任,诬加到张献忠身上”。③
2、被指犯过“投降主义”的“严重的路线错误”
张献忠曾在谷城投降明朝,故“文革”期间曾被指犯了“投降主义”错误,同《水浒传》中受招安的宋江联系在一起。如1976年的一本《<水浒>评论集》中说:
“张献忠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弯弯曲曲的。他对明王朝抱过幻想,接受过“招抚”,并企图劝说李自成也接受“招抚”。张献忠的这一步走错,不仅使自己掉进了旋涡之中,并使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了低潮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路线错误……”最终张献忠“克服了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,在走过了一个‘之’字形的道路之后,重新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……”④
总体来说,此一时期,张献忠的历史形象是正面的。
回归史料,近年来学术界不再讳言张献忠对民众的屠杀
1、80年代,学术界在肯定张献忠“打击封建势力”的前提下,承认其“戮民”
1980年3月,举行了一次“张献忠在四川”的学术研讨会,主要讨论了“张献忠在四川‘杀人’问题的真相,张献忠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,张献忠失败的原因等三个问题”。⑤与会者一致认为,张献忠“伪降”明朝只是一种斗争策略,无损其农民军领袖地位。也有学者在会上承认,张献忠确曾屠杀民众。如田培栋在《对张献忠“屠蜀”应重新予以评价》一文中说:
“多年来,有些人又走向另一极端,不加分析,毫无批判地全部肯定张献忠‘屠蜀’是革命行动,凡是被杀的人,都是罪有应得,这样的结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。根据大量的材料,可清楚地看出,在被张献忠所杀的人当中,不一定都是反动派,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辜的,实属错杀。”
一方面承认其“农民起义领袖”地位,一方面也强调其“戮民”事实不容否认,是此一时期学术界对张献忠评价的主要变化。如李三谋在《明末大西军在四川“屠戮生民”之问题》一文中说:
“记载张献忠‘戮民’过多的史料不下百种,凭空一概否定,全然抹杀,是难以令人信服的”“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领袖,虽然摧毁了明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,可谓打击封建势力甚为有力,而对于大西政权统辖下的四川这块革命基地的建设颇为不够,甚至是有损伤”。⑥
再如,胡若曦《“张献忠屠蜀”考辨》中说:
“张献忠起义军的打击对象是反动势力,是地主、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,这有什么不应该?当然,也要看到,农民义军在这一过程中,不仅杀了地主本人,也往往杀了他的全部家口,打击面很大,杀的人相当多。这是从农民的朴素的阶级仇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明的。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的革命性,更不能加以夸大,诬说起义军见人就杀,把四川人杀光了”。⑦
肯定张献忠的“农民起义领袖”地位,是此一时期学术界讨论其屠杀行为的基本前提。如王纲在《论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革命性》一文中说:张献忠政权“虽然有那样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,但是,它作为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存在于明末清初,却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。”⑧
2、近年来,学术界开始直言不讳评价张献忠“暴虐成性”“手段残忍”
近二十年来,张献忠的历史形象再起变化,其观点与晚清、民国时代趋同。在2006年发表的《张献忠的一桩公案——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》一文中,作者耿法梳理了大量史料,直言道:
“(张献忠)此人暴戾成性,反复无常,目光短浅,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和见识,导致他后来一手制造了数起灭绝人性的大惨案。他当了短命的偏居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对四川百姓当然是个灾难,但相对来说又实在是件幸事,因为他的权力所限只能危害四川一地;倘若他真的成为中国一代帝王,建立了一个朝代,那么必然是一个祸害全国百姓的暴君,罪恶将大得多……”。⑨
2015年,张位东从心理分析角度,撰成《张献忠屠蜀原因新论》一文。文章认为:张献忠“行为之变态,手段之残忍,毫不掩饰自身变态的心理”,如使用所谓“骑木驴”杀人——“将女子吊起,下置一木杆,割绳坠落,木杆从阴部贯之,鼻口而出,遭此行之女,折磨三四日之后才死去”。“从张献忠的古怪性情和行为举止,还能略推其精神异常”“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知觉障碍,出现愤怒、忧伤、惊恐、逃避及攻击的情绪和行为反应”。
有学者批评了此前数十年的张献忠研究:
“国内的史学界在研究评价张献忠时,极尽美化神化之能事……煞费苦心地把他打扮成高大全式的历史人物……对当时的亲历者、参与者、目击者传下来的真实的血腥记录,一概斥为‘诬蔑不实之词’。……(历史研究必须)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,得出科学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,而不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,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任意涂抹。”⑩
此次“江口沉银”众多出水文物中的金耳环、发簪、金戒指、手镯等,均是张献忠政权掠夺民众的最直接证据。张的历史形象,随着此次考古发掘,终将定格。
注释
①任乃强:《张献忠屠蜀辨》,见于《张献忠在四川》,《社会科学研究丛刊》编辑部编,四川省新华书店1981年,原载1947年《社会月刊》;②谢国桢:《农民起义与张献忠》,《历史教学》1952年第2期;③孙次舟:《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》,《历史研究》1957年第1期;④康立:《论<水浒>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反动作用》,见于《<水浒>评论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;⑤王家楼:《关于“张献忠在四川”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综述》,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0年第3期;⑥李三谋:《明末大西军在四川“屠戮生民”之问题》,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8年第2期;⑦马芸芸:《略述60年来的张献忠研究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10年第4期;⑧王纲:《论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革命性》,《四川社联通讯》1983年第5期 ;⑨耿法:《张献忠的一桩公案》,《书屋》2006年第9期。⑩杨培德,《关于梓潼神庙内的张献忠塑像》。